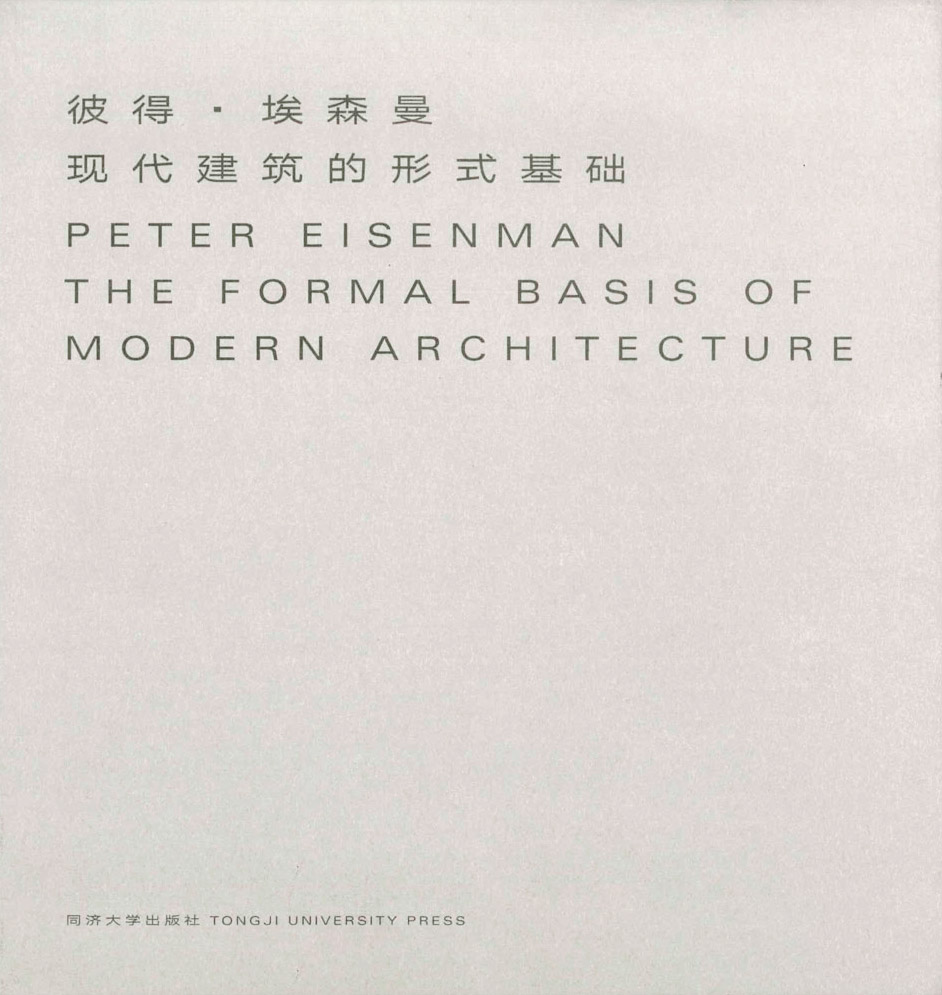
彼得·埃森曼《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
译者序:困局与揭示
罗旋
只有在刻意回首过往的时候才看得明白,一部作品真的就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
——约翰·海杜克,《美杜莎的面具》(John Hejduk, Mask of Medusa)
所以,在我们所居世界的另一端,或许竟存在这样一种文化:它醉心于空间的秩序,但却将万千存在之事物归于我们不能名、不能言、不能思的范畴。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2016年夏天,彼得·埃森曼在整理工作室的时候,无意间找到了四十多函尘封已久的柯林·罗(Colin Rowe)的来信。这些信件写于1963年,其时埃森曼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而书信的内容正是罗给这篇论文的反馈。罗在其中一封信中向埃森曼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你所说的‘原理’不是普遍适用的吗,那为何要单独强调‘现代’?”虽然信纸早就泛黄,但是导师柯林·罗的字句透过名曰“威望精英”的打字机字体,如今依旧入木三分且不留颜面。而埃森曼最终的论文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也不动声色地挑战了他的老师。
在论文完成四十二年之后的2005年,这本《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终于以德文译本的形式首次付印。次年,英文原著才通过原版影印的方式出版,其格式和内容完全忠于最初打字稿的样子。由于此前从未完整发表,这篇论文在此间四十余年里变得颇具神秘色彩。埃森曼本人回顾过往,认为这篇早早落笔却又姗姗来迟的论著是他写过的最重要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本书。该书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基于文字阐述,铺陈了一种理论架构。它包括导言以及“形式之于建筑”、“一般性建筑形式的属性”、“形式系统的发展方式”等三个章节。第二部分则结合文字和图解对八个案例进行了形式分析,这些案例来自四位现代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阿尔瓦·阿尔托、勒·柯布西耶及朱塞佩·特拉尼。
选择这四位建筑师,无疑是作者当时内心思想挣扎的反映。赖特和阿尔托这两个选择可以说是埃森曼对他的官方导师莱斯利·马丁爵士(Sir Leslie Martin)作出的艰难妥协。据杰弗里·凯普尼斯(Jeffery Kipnis)所说,作为一名现代主义风格的坚定倡导者,马丁曾试图“将埃森曼的博士论文推向抒情而人文(lyrical/humanist)的方向”。[1] 另一方面,柯布西耶和特拉尼这二者则反映了来自柯林·罗的形式主义影响。正是1961年夏天与罗一同游历欧洲的经历,让埃森曼学会了通过“精读”来看见建筑中的“不可见”。[2] 他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思想相互角力的产物——人文主义还是形式主义?前者最终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后者则成为批判的方法。但是,由于罗的形式主义手段依旧离不开一种预设的、不容辩驳的人文主义式的理想化倾向,他的形式主义对于埃森曼来说是不够彻底的。虽然罗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是埃森曼已经开始质疑其理论是否足以帮助他来理解、分析以及架构建筑学的根本问题。
关于罗的质问——既然原理是普适的,为何要单讲“现代”建筑?——埃森曼在论文导言中是这样回应的:“论文中出现的‘现代’一词作为限定语仅仅是对所选案例的指称;文中讨论的‘原理’应被理解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3] 这句话看似表达了对罗的认同,但他似是而非的语气却让人读下来渐生出一丝疑惑。他强调了“现代”作为形容词的语法功能,表示它只是某组案例的标签,仅此而已。这句话刻意且断然地简化了“现代”一词本该具有的更为复杂的意味。他的话暗含了一种保留,甚至是回避的态度。留白处显现出更多疑问:是何种共通性质(风格、时期、意识形态抑或是其他?)使得一系列建筑以“现代”之名被归于同一范畴?“现代”这一具体概念中存在哪些内在特性,使其可以成为构建“一般性”建筑原理的范例?最重要的是,到底是何种条件促使“现代”这一概念本身开始受到质疑?
论文构写于60年代初,此时理想与宣言的装潢正从现代主义苍白的墙体上褪落,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愿景正欲崩颓,伴随着彻骨的历史割裂感,知识分子纷纷从集体的幻象中抽离开来:西方社会正在普遍经历一场“知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文化生产和社会变革在1968年达到决定性阶段,后来有诸多著作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特殊性。[4] K.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在他编著的《1968年以来的建筑理论》(Architecture|Theory|Since 1968)中写道:“自1968年以来……文化——作为一种既属于个人又被个人拥有的东西,作为一种使自身领域之内一切事物自上而下地趋于饱和的沉淀物,作为合法性与反权威之间的界限——将不再能如我们期望的那样自发地出现了,亦将不再是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它现在必须通过更自觉的理论程序来不断地构建、解构和重构。”[5] 埃森曼完成于1963年的论文显然与同时期西方诸多学术项目共用了同一种理论语汇。在1963至1968这短短五年间,理论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其中就包括符号及语言学研究——如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Roland Barthes, 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1964)和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Noam Chomsk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5);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如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Louis Althusser, Pour Marx, 1965)、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1966)以及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1967);精神分析学论述——如拉康的《文集》(Jacques Lacan, Écrits, 1966);后结构主义批评——如福柯的《词与物》(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和德里达的《论文字学》(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最后,影响后世的建筑理论著述——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Aldo Rossi, 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 1966)、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Robert Venturi,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1966)以及塔夫里的《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Manfredo Tafuri, Teoria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1968)也都问世于这个时期。而在所有这些著作出版之前,埃森曼就已经完成了《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可以说,他的这部论文预见了一种新的建筑理论的到来。
就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而言,上世纪6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不只是顺理成章的时间推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危机”时刻。埃森曼的“原理”,也就是形式之间的一系列不可化约的逻辑关系,正是这一危机之下的产物。骤然兴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是一整套试图认识人类知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思想模型。可以窥知,埃森曼的“现代”概念正是一个奠基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内向理论建构。他所倡导的建筑学,针对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某种结构性转变,他的建筑理论亦是对上述这一知识论断裂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埃森曼与其他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知识分子同时期的理论工作是异曲同工的。
在整个论文的导言部分,埃森曼开宗明义:论文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是扑朔迷离的 “现代”概念在历史面前的复杂状况,即反思“现代”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全文以对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一书的精要讨论开篇。就学术方法和风格而言贝克尔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历史学家,但他与欧洲同时期的思想先驱,如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等人也多有共鸣。在这本短论中,贝克尔将欧洲启蒙运动视为“现代性之种种幻觉的最初源头”。[6] 埃森曼在援引贝克尔的时候,把他的名字“Carl”误拼为了德语式的“Karl”,仿佛他的解读中已不自觉地揉合进了从柯林·罗那里继承而来的德语系形式主义思想。
埃森曼写道:“在贝克尔的描述中,现代‘思想气候’(climate of opinion)是基于经验(factual)而非理性(rational)的:整个环境充斥着现实的内容(the actual),以至于理论的内容(the theoretical)轻易地遭到忽视。对贝克尔来说,历史——即事实及其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已经取代了推理与逻辑——即‘为什么’的问题。”[7]
“思想气候”是一个17世纪的术语,贝克尔将之类比于“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个词,指的是加诸世界之上的“某种特定的运用智识的方式和某种特殊类型的逻辑”。[8] 该定义本身就已经内含了对所谓的“历史的科学客观性”的怀疑,这一点与“知识型”(episteme)这个概念颇为类似。假借着贝克尔的论述,埃森曼列出了关于“现代思想气候”的三组对立概念:“经验的”与“理性的”、 “现实的”与“理论的”、 “历史”(即“是什么”的问题)与“推理和逻辑”(即“为什么”的问题)。乍看上去,埃森曼的论辩框架刚好可以纳入海斯所描述的“‘理性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之中。[9] 不过,如下文所述,这三组表述或许比它们看起来要更复杂一些。针对“现代”与历史的辩证关系问题,埃森曼不动声色地对贝克尔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改写,正好足以把他的个人看法夹带其中。通过对比埃森曼改写的段落和贝克尔的原话,本文有三点观察,并相应地从中得出了三条“原理”。
我们先看第一条。贝克尔指出,历史学中有两种倾向。其一是所谓的“新兰克主义”(neo-Rankean)史学,这种倾向由科学式的历史实证主义所操纵,崇尚冷峻的客观事实;其二恰恰相反,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倾向——贝克尔所秉持的正是这种史学观念。他认为,事实绝非不言而喻,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最好的概括就是他的这句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埃森曼在他的改写中毫不犹豫地重述了这一组对立,用琼·奥克曼(Joan Ockman)的话来说,他区分了“作为真实的历史”与“作为观念(concept)的历史”。[10] 尽管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由一系列具备了某种客观性的历史事件所诱导的社会状况(如同现代历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所捍卫的那样),但是在另一方面,与现代性不同,现代主义乃是对特定观念下的某种现代性在艺术层面的回应——就现代主义而言,真实(thereal)从来都是触不可及的。按照埃森曼的设想,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向真理的某些方面,其唯一的途径是概念建构(conceptual framing)。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就此得出埃森曼的现代主义的第一条原理:现代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
第二,按贝克尔的原话,世界看起来“一直都在演进之中、一直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11] 相比之下,埃森曼对贝克尔的重述则是这样的:“他把世界看作一条恒变不息的时间序列……永无终结。”[12] 贝克尔的话暗含的,是一个有目的的历史,在他那里,历史的终极目标有待实现。而到了埃森曼这里,他偷换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而消除了历史的目的论。多年以后,埃森曼在他1984年的文章《古典的终结:起始的终结,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中又回到这个问题,明确批判了历史的目的论假设。他指出,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谬误,在于“现代人……在思想上陷入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时代就是永恒”。[13] 现代人有赖于这种似是而非的永恒感来为其建筑学赋予合法性。这样一来,为了破除这个幻觉,现代主义必须将其自身重新奠基于一个开放式的历史框架之上。因而,我们得出了第二条原理:现代主义历史是前瞻性的。
第三,贝克尔称,既可以用一种历史视角观察世界,也可以用一种科学视角观察世界。然而,在这两者中,埃森曼略去了其中一种,而仅仅保留了历史这一种解释世界的视角。按照贝克尔的表述,科学视角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或者叫功能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埃森曼将科学归入历史之下,言下之意是科学和历史的对立(进而也就是“理性主义者”和“历史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尖锐”。这一隐晦的假设在贝克尔处也能找到验证:“历史学和科学这两者的兴起不过是同一动因之下的两种结果;现代思想存在这样一种趋向,即避免对于事实进行过分的理性化处理而趋向于以某种更为缜密和中立的方式考察事实本身,而历史学和科学正是这种趋向的一体两面。”[14] 这样一来,按照贝克尔的论述,现代科学和现代历史学这两者是同一种实证主义倾向的产物。后来,埃森曼曾在《古典的终结》一文中将功能主义批判为“立足于某种科学与技术实用主义之上”。[15] 与那种目的论式的历史主义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貌似不证自明的实证功能主义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即二者都仍然受限于一种人文主义式的理想化倾向的桎梏,这两种建筑学无外乎显现为一套“伦理层面上的赋形之法”。[16] 于是我们就得出了第三条原理:现代主义是对理想化倾向的拒绝。
现在,我们把埃森曼的三条原理整合起来——现代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现代主义历史是前瞻性的以及现代主义是对理想化倾向的拒绝——就能得出:现代主义是一种拒绝理想化倾向的前瞻性历史理论。由此,对于上文中罗的质问——“既然‘普适’,为何‘现代’?”——埃森曼把问题本身颠倒过来,以反问做出回答:“既然‘现代’,为何‘普适’?”必须对那种普适的、人本的理想化倾向加以拒绝,而这么做就必然会导致对客体自身内在逻辑的皈投——简言之,就是建筑学的形式逻辑。不过,尽管埃森曼拒绝普适性,但他也并没有完全把他导师的看法弃之不顾,终究还是坚称,应该认同《形式基础》中所提出的形式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埃森曼还是认可了普适性的必要性,尽管普适性这个概念因其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存在诸般问题,但为了幻想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普适性却又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的,出于“为形式的有效识别提供根据”的目的,[17] 埃森曼也不得不暂时接受格式塔心理学中感知法则的普适性,即使他把“先在的几何形体或者柏拉图形体”认定为“人文主义理论的残留”。[18]
上述有关普适性的内在悖论体现了马里奥·盖德桑纳斯(Mario Gandelsonas)曾指出的“目前建筑学意识形态的内部矛盾”,以及建筑学自身学科构成的高度虚构性。[19] 建筑学既是建筑物的构造之学,也是概念的建构之学——这一点并不是社会层面、美学层面、技术层面或者伦理层面上的理之当然,而唯有通过理论层面的重新架构或重新奠基,建筑学才得以如此这般地彰显其自身。通过理解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知识论危机之下的“现代”概念,埃森曼达成了一种属于建筑学的解决方案,它尝试脱离人文主义理想性的束缚,进而豁免于沦为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负担。埃森曼构想出了一种自足于现代的形式理论,并找到了具体确切的方式来揭示其自身的“建构性”(constructedness)。这就是他给罗的答案。他的形式基础就是这样转译成了建筑学。
那么,这其中又有哪些值得转译成中国的建筑学话语?了解埃森曼作品的人知道,要想理解他的形式理论而不沦为肤浅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就必须熟稔纵跨整个西方建筑史的形式脉络及其内在逻辑,这条形式脉络跨越了从维特鲁威到阿尔伯蒂、从克劳德·佩罗到皮拉内西、从勒杜到勒·柯布西耶的整个历史。既如此,对于栖身“世界的另一端”(如福柯所说)[20] 的我们而言,埃森曼的这样一个全然奠基于西方经典之上的理论项目又如何为我们自己的建筑学带来助益呢?
或许埃森曼的博士论文并不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但它足以做到的,是吁请我们把注意力从理论作为一个工具的用处转移到理论本身上来。如果我们仅仅把理论看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那么多半情况下,理论都难免沦为由外在因素所裁夺、所操纵的傀儡,为某个受控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服务。例如盖德桑纳斯所论述的,“普适性”这个概念就是用来遮蔽一个明显而重要的事实,即建筑学知识向来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由主流文化中的特权阶级所拥有、生产和逐级分类的。如果回避了这一事实,那么就很可能会简单地移植和复刻埃森曼的这类形式概念,进而仅仅流于“形式”,而没有意识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建筑学本身早已在某种话语中身陷低人一等的位置。正如盖德桑纳斯在提及中国哲学家张东荪的《中国式逻辑》(La logique chinoise)一文时所指出的,这种“低人一等”的状态“所揭示的唯一事实,就是概念体系的匮乏”。[21] 埃森曼的博士论文所示范的,正是克服这种匮乏状态的一种可能。通过从内部向普适性理念提出质疑,埃森曼的论文揭露了现代建筑的根本性困局(aporia),进而迫使读者不汲汲于浅显易得的内容,而开始把关注点从图像化的建筑外观向下深入,深读建筑。像阅读文本一样阅读建筑,哪怕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龃龉与支吾、繁复与缺漏、理屈和词穷,这无疑是在概念上和智识上批判性地破旧立新的第一步。埃森曼和罗的隐微对话贯穿于他的博士论文全篇,来往之间,他逐渐找到了一个远离核心的位置。就此而论,我们虽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西方建筑学的局外人,但也正因如此,反而受惠于旁观者的身份而有望施展同等水准的批判力量——不仅仅从西方建筑学的外部,更是在中国建筑学的内部。埃森曼在知识论断裂的破晓写就此文,而此时此刻的我们也身负同等紧迫的任务。有鉴于此,今天的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必应背负着一种责任感。
1 Jeffery Kipnis, “By Other Means,” in By Other Means: Notes, Projects, and Ephemera From the Miscellany of Peter Eisenman, ed. Mathew Ford (Leiden: Global Art Affairs Publishing, 2016), 19.
2 Peter Eisenman, “Introduction,” in The Formal Basi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Baden: Lars Müller Publishers, 2006), 19.
3 同上
4 是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若干以学生和工人为主的群众运动,笼统来说,这是西方日益激化的社会阶层矛盾以及民众与体制权威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所引发的结果,也是冷战时期充斥着矛盾和非理性的政治现状的表征。当大多数人开始承认现代主义已经无法承载它所允诺的社会理想,文学和艺术便由外向的空想退转到了内在的反思。不过,具体的年代和事件终究是历史叙事中的一种记号,这一时期的特殊性的种种成因及其在各学术领域中的表现方式已远超出本文篇幅的限制,这里权将其视为一种自证的结果。
5 K. Michael Hays, “Introduction,” in Architecture|Theory|Since 1968, ed. K. Michael Hay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x.
6 Johnson Kent Wright, “The Pre-Postmodernism of Carl Becker,” Historical Reflections / Réflexions Historiques 25, no. 2 (Summer 1999): 323.
7 Eisenman, The Formal Basis, 11.
8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 5.
9 Hays, Architecture Theory, x.
10 See Lucia Allais, “The Real and the Theoretical, 1968,” Perspecta 42 (2010): 32. See also Allais’s references to 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New York: Rizzoli, 1993) and Joan Ockman, “Talking with Bernard Tschumi,” Log13/14 Aftershocks: Generation(s) since 1968 (Fall 2008): 159–170.
11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27.
12 Eisenman, The Formal Basis, 11.
13 Peter Eisenman,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 Perspecta 21 (1984): 163.
14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20.
15 Eisenman,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157.
16 Peter Eisenman, “Post-Functionalism,” in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ed. K. Michael Hay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237.
17 Eisenman, The Formal Basis, 17.
18 Eisenman, Post-Functionalism, 239.
19 Mario Gandelsonas, “Linguistics in Architecture,” in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ed. K. Michael Hay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121.
20 Michel Foucault, “Preface,” in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xix.
21 Mario Gandelsonas, Linguistics in Architecture, 121.
彼得·埃森曼
Peter Eisenman
Peter Eisenman